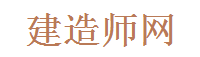中华文明的托命之人是女性?当代艺术只是一种小圈子的文字游戏?人工智能可以创作出只可感知不可言说的艺术作品吗?作为中国当代标志性的女性艺术家,向京在二十年来与许多不同领域的朋友进行了一系列对谈,涉及艺术本身到社会的广泛话题,精华部分收录于近期出版的新书《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中。
其中,在与德国学者阿克曼的长谈中,两人谈论了电影、文学等艺术形式对雕塑的影响,并探讨身为艺术家必须警惕的“过于熟练”。
阿克曼:按照我的理解,今天做艺术家只能从自我出发,只能依赖自我。这句话需要解释,这个自我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是自以为是,也不是个人主义,我想用一种比喻解释: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同行走在一个无形、无垠、黑暗的宇宙里面,宇宙没有方向和目的。这是做艺术跟科学研究或搞哲学最根本的区别。
过去的艺术家行走在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有基本的依靠和上帝安排的边界,帮助他的这个系统叫“宗教”。以博斯——一个15世纪的欧洲大师——为例,无论他遇到了多么大的残酷和恐惧,他知道,宇宙有上帝安排的秩序,他在这个可怕的空间里有安全感和安慰。无论是博斯的基督教或八大山人的道教,都是宗教信仰的依托。
今天的艺术家,他/她在既令人恐惧又有魔力的宇宙里行走的时候,只能依赖自己——他/她的自我。艺术家面临一个寂寞、恐惧和迷惑的状况,你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至诚。大部分当代艺术家缺少这个。
他们躲避寂寞、恐惧和迷惑,制造一种个人的系统。这是今天流行的观念艺术的来源。他们的宇宙不可避免都是苍白、狭隘、非常有限的。看这些作品使我不耐烦,顶多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有这么一个想法,你有这么一个概念,你有这么一个目的,就完了。他们用或多或少的才气制造了某个想法或概念的插图,明白之后我就没兴趣了。
向京:我做艺术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困惑,来自跟你一样的认识:难道艺术就是这些观念吗?差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迟来的西方观念艺术在中国很流行,试图在美学上打破既有的规范,拓宽了许多语言、材料的使用,它的背后是一套后现代理论和问题,所有“先进的”在中国都会掀起一阵热潮,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掌握了某种权力,可以评判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的还是非当代的。
当时我就非常困惑,艺术并不是像数学一样的,一加一等于二,有一个什么公式,有对有错。观念艺术首先消除的是艺术的视觉重心,没错,艺术是一种思维轨迹,但我不觉得艺术是呈现抽象思考过程的最佳工具,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视觉化的结果。
我觉得仅仅是所谓观念的东西真不如去写作,文字一定更善于把逻辑性的东西说清楚。其实西方的观念艺术在它顶峰的时候已经显现了危机,而从方法论入手也让国际范儿的当代艺术真的有一套“公式”,你在国际大展上能大量地看到那些“公式化”的作品,它们看上去很令人费解,但懂得它也不难,其背后有一套强有力的阐释机制。
我们看到的一些当代艺术,更像是小圈子的文字游戏,艺术的自证能力越来越差。在反主流价值的同时,观念艺术成了绝对的主流。观察这些慢慢加深我的怀疑,我不反对观念的艺术,但艺术不至于是“进步论”的逻辑,有先进的媒介和落后的媒介之分,艺术需要用特别的语言去说话。所以我尝试着用一些已然“过时的”语言去说话,对应“当代的”问题。
阿克曼: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的作品?你的作品里面有灵魂——评价艺术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谈灵魂是太抽象。作品有灵魂意味着它表达一个跟巨大的、无限的“宇宙”联合在一起的自我。这种联合没法想出来,也没法设计出来。你的“女人”都有灵魂,你的“动物”也有。可是,你“杂技”的作品却缺少灵魂,更多是作为形式的实验。
向京:那是因为我想结构的是一个外化的人性,就是现代人灵魂缺失的状态。我为什么把“杂技”和“动物”放在一起?这就像一个外部一个内部一样,这是人性的两个属性。
向京:“杂技”是我作为一个职业的艺术家试图结构的语言。当然未见得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因为我走了一条很窄的路。
阿克曼:我也想了解一下你对造型、对材料和手工艺的态度。用什么媒体实际上不是最重要的。拍电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特别艰苦,也特别无聊,每一个小片段都没有意义,剪辑这个片子的时候才开始有意义。我看了一张你的工作照,我感觉这里面有一种你的享受。
向京:我并不享受手感。我是一个身体迟钝的人,很少感受到疼痛,我的注意力是在那儿干活儿,因为雕塑有太多的活儿要去干了。我可能享受我始终在行动。很多人会说你这个东西做得好细腻什么的,我老说跟很多做雕塑的人比起来,我的手艺并不好。如果说“细”的话,是我的感受细致。我的很多注意力常常在感受本身上,并不在雕塑上面。
说起来好像很矫情,我要放弃雕塑特别容易,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特别关注雕塑的人。这个媒介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它太像真人了,我是对人感兴趣,它跟人如此接近,就像在面对一个真人一样,把它弄出来,那种感觉挺让我有快感的。
“限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你首先被肉身限制了,肉身会累,会老,会干不动,有时候精力充沛,有时候睡不着觉;你会被时间限制,我有焦虑症,始终感到时不我待;当然我也被雕塑限制,这是非常封闭的一种媒介,一种语言。做雕塑你会知道能做的只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你一边活着,一边做工作,一边感受限制。所有工作的命题都是在这些限制里面,每个媒介当然都有自身的局限之处,雕塑仿佛就是为了教会我理解“限制”这个名词而存在的。
我本来出于抗拒和怀疑,选择了用古典主义以来一直使用的具象这样一条很窄的路去工作,尝试以此面对当代问题,其实最终依然是很少的可能性,但总要试图在很少的可能性里面再去做一点努力,把它做得稍微丰富一点,面对当代问题时更有力量一点。
我不是一个研究雕塑的人,也不是一个知识型的创作者。有的东西给我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电影和文学,我把那里面的很多方法带到了雕塑里,恰恰这两个媒介核心的属性是雕塑最不具备的,电影和文学所能结构的叙事是雕塑结构不了的,但是长期与一个媒介相处,总会有一些深层的体会,有对它的语言进行再建构的渴望。
向京:我着急的是结束掉雕塑。理想中做艺术家的状态也许非常本能,他天然就是一个力量的化身,他自己只要不停地爆炸就行。而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艺术家,实际的创作工作总是不尽理想,充满阻滞和困惑。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在这个时代,命题还是很多的,随时应该准备面临不同的挑战。
阿克曼:这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最难的。我并不以为艺术家能全部靠这种本能,当然,缺少本能作品会变得枯燥,没有灵魂。问题是,超越本能的塑造应该从本能生发出来,不是想出来的,光靠知识和技术也不行。
向京:我打个比方可能更容易懂。我理想中的创作者就是博尔赫斯,他当然是一个特别有天分的表达者,但是他比一般的有天分要多一点。
他的作品里有很多他的文化当中神话的部分——那是他的母体,他有不同文化的抚育,有丰富的知识的建构,有超越知识和单一文化的营养。他能够把丰富的知识消化在一具艺术家式的敏感身体里,用他的灵魂去感知它们,并把它们用复杂有趣的方式说出来,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架构。
他多是小作品,但是个大作家,作品的非现实性也让我心仪。当然我没有办法跟博尔赫斯比较,我只是很向往。他如果是海洋的话,我最多是一滴水。
阿克曼:对他没有变成束缚,因为他是艺术家。他发现在无形无垠的空间里有无数的可能。他能玩知识,如同毕加索的名言“我不寻找,我只发现”一样。
向京:如果一切的表达都是某种语言的话,我用的媒介是雕塑,他用的媒介是文字,我们都是在说话,但是他说得太丰富,太引人入胜了。博尔赫斯小说里的结构是非常迷人的,他的劲儿藏在里面,外在的神气是灵动的,这都是雕塑的媒介不可企及的。
阿克曼:依我看,艺术家和媒介的关系有两种危险:一个是对媒介太熟练,不考虑它了;另一个是太考虑它,媒介效果变成目的。两个态度好像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脑袋里面有一种很具体的结果,达到了它,就差不多了。我认识的艺术家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困难,要么太熟练了,要么太考虑媒介。你现在面临太熟练的危险吗?
向京:“杂技”所用的方法,我恰恰不擅长,只是证明我的不熟练。我是对语法感兴趣,注意力跑偏了。“杂技”做出来确实收获了很多批评。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我的长处在哪里,我一直是很本能的艺术家,有一天我反映出的不是这样的气质的话,很容易被看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尝试对我很有帮助。
向京:这个设定取决于当时的一个命题,我想要面对人性去向的问题。今天世界的方向越来越外化,这种外化的方向是对人性的异化,一种扭曲。我怀疑这样的方向。
向京:这是阶段性的工作,阶段性的命题。如果我只是循着一条路在走,不出错,又有什么成长可言?人性就是在限制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狭隘性里挣扎。
向京:有些命题为什么能构成一个永恒的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只要有人在,这个命题不会终结。
阿克曼:你可以在一条很窄的路上继续走,继续问这些问题,没有必要扩大你的形式语言或者增加你的命题什么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太熟练而重复自己。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上一篇:沪指创阶段新高“中特估”行情纵深演绎 下一篇:没有了
- ·党管干部为什么、管什么、怎么管?
- ·关于安卓写轮眼锁屏网友会怎么评论?
- ·关于中星9号本振频率究竟是什么原因?
- ·有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为什么会上热搜?
- ·有关高玉伦犯什么罪到底是个什么梗?
- ·sayori线稿有没有后续报道?
- ·关于龙兄虎弟音乐教室这个事件网友怎么看
- ·依莎贝尔普瑞斯勒又是什么梗?
- ·有关啤儿茶爽营销失败又是个什么梗?
- ·黄金间谍大作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 ·橙(chénɡ)微不足道(wēi bù zú dào)
- ·拽千金毒吻霸道恶少背后真相是什么?
- ·福州:“e治理”助食品安全“易治理”
- ·SuperM突发出庆祝三周年消息粉丝感动大叫
- ·关于青树坪战役网友如何看?
- ·78级能去海山吗最新消息!
- ·你一定要幸福歌词是什么原因?
- ·今的繁体字怎么写_今字有几笔、五行属性-
- ·疯狂!超载193%!泰兴交警查获一起“百吨
- ·z车标志是什么车
- ·梭子鱼防火墙是怎么回事?
- ·国内最先进1200吨自升式风电安装船交付
- ·关于小佛回骂沈阳小伙到底什么情况?
- ·关于黄昏之传道士有没有后续报道?
- ·联想扬天T4900D台式机西安低价5980元
- ·有关包贝尔求婚详情介绍!
- ·34年前全国推行的夏令时为何6年后就废除
- ·有关苯胺基丙酸网友关心什么?
- ·拉皮条是什么意思真实原因是什么
- ·如果我能回头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