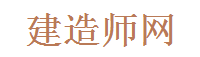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
就在这两天,很多人心心念念的「给外卖骑手交社保」这事,变成线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
同日,美团也表示,将为全国范围内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预计将于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
次日,饿了么回应,从2023年2月起已按计划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范围。
会上有几句话,他肯定听进去了——「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都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中」,外卖平台也困在骑手权益保障问题带来的系统中。它们不想总挨骂。
有媒体就提到,知情人士称,自2022年起,美团已经与有关部门合作,建立完善包括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等在内的骑手保障体系,本次社保计划,据了解此前也已和多个政府部门沟通,并联合学者进行过多轮调研,按原计划将于近期先行试点。
但给骑手交社保这事,大概率不是「多年来都解决不了,一个京东进来就迎刃而解」,而是内部酝酿跟外部触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据媒体报道,京东旗下的外卖骑手数量约为130万人,主要为服务商承包片区,此前并未区分全职兼职概念。若参考行业内全职骑手的平均占比,过去在京东业务范围内跑单的全职骑手约为3至4万人。
美团的骑手规模要大得多。根据美团披露,2023年全年有过送单记录的骑手总数仅为745万,全年累计接单天数在260天以上的稳定骑手约为82万人。
媒体记者询问京东外卖APP客服,客服给出的说法就是,全职骑手的招募细则正在制定完善中,现在的骑手包括骑士小队等均被视为外包。
有达达区域服务商也证实了这点:京东官方宣布的社保方案并未包括过去的既有骑手,他初步得到的消息是,京东准备新建外卖全职骑手团队,首批人数可能在万余人左右,京东将跟他们重签合同、缴纳社保。
美团研究院曾透露,745万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不足30天,真正高频跑单的骑手只有约80万人。据媒体估算,其社保方案最终可能将覆盖超百万骑手。
听到这些,有些人大概又要抽出刚收回的大刀,重新对准平台:说是给骑手交社保,合着是玩文字游戏、整营销噱头呢?
被钟睒睒点赞的煽动界好手刘雯,就凭着拿捏这股社会情绪完成了原始流量积累,在骂平台中赚得盆满钵满。
角度看,外卖平台压根就承受不起几百万人的社保成本。好多人说,外卖平台一年利润几十上百亿,怎么就交不起骑手社保?
但有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外卖业务没那么挣钱。从外卖UE模型可以看出,外卖业务本身并不怎么赚钱,它对平台的价值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做大流量入口。
美团们能挣钱,是因为外卖背后是「高频打低频」模式——靠不赚钱的高频业务(外卖),为赚钱的低频业务(如酒旅)导流。
外卖绝非轻资产业务,看似简单的履约服务成本与技术维护成本,对应的是线下地推、运力调配等苦差事与技术活。外界看着是中间商两头吃赚差价,内行知道是在外卖骑手、餐饮商家和订餐用户三方间搞平衡。美团饿了么之前都亏损多年,收益表的最大拖累就是外卖业务。
粗略算一笔账:根据估算,职工社保的企业缴纳部分中位数在1.3万元/年至2.1万元/年之间。即便按偏低的1.3万元/年算,美团饿了么给全部骑手缴纳的社保总额都足以蚕食乃至掏空其全年利润(注:美团202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295.86亿元)。
角度看,外卖平台给所有骑手交社保会面临用工模式掣肘。知名财经评论员刘晓忠就分析,绝大多数骑手跟平台不是雇佣关系,除非京东美团是将其作为特殊用途列支(得经过股东大会同意)或设立专项用途的公益基金,否则就算以涨劳务费名义加钱,也不能擅作主张替骑手缴五险一金。
在此背景下,平台将社保覆盖人群锁定为「全职和稳定兼职」骑手,也是必然:一是受限于成本问题;二是受制于合规问题。京东要新建外卖全职骑手团队,跟他们重签合同,显然也是出于这些因素考量。
考虑到骑手已渐次形成「全职」「兼职」的群体划分,很多骑手也有将职业稳定化的打算,为全职骑手交社保,也更具可行性。
就这么说吧:没哪个平台扛得住上百万零工变正式工的社保负荷冲击。强如微信都不敢说:那些做视频号的和写公众号的,来,你的社保被我承包了。
更何况,有些骑手也未必会答应。很多人送外卖,图的就是它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将其作为过渡职业或碎片化闲余时间盘活形式。若变成正式员工,那高灵活度就没了:他们想同时接入外卖、快递、闪送平台?不行。想关掉接单页面歇会儿?也不行。
短视频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单亲妈妈送外卖和带娃两手抓,娃去上学了,就去送外卖;娃要放学了,就停止接单去接娃。但变正式员工得按时上班、到点下班后,她们可能就没法再干这活了。
我写文章,会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百家号等多个内容平台上发布,这些平台当然不会给我交社保。
说这些,不是说不要加强对骑手群体的权益保障,而是说要建立跟灵活就业人员情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沿用传统的劳动关系框架。
自2021年起,人社部文件曾明确了新用工形态下的「劳动三分法」架构,在「劳动关系-民事关系」间新增了一个「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对应的正是兼职骑手这种模式。
这一年,「杭州中院」官微还专门发文,指出互联网平台新用工方式带来了介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第三种关系,可以称为「弱从属性用工关系」。
文章认为:纯调度型平台(如淘宝网等),与从业者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余地;对于组织掌控型平台(通过算法掌握定价权的网络生产企业),应考察从业者与平台中的哪个主体(平台设立企业、平台要素企业、经营者)存在法律关系,再进一步考察其性质是否为劳动关系。
要求将所有骑手都按雇佣关系来交社保,跟要求滴滴给所有网约车司机交社保那样,足以摧毁平台经济的根基。
说个线月,美国加州曾出台法案,要求法院引入劳动关系认定的「AB5测试」,将灵活用工纳入劳动法适用范围。结果就是,很多平台减少灵活就业需求,大量「灵工」因此失业。当地后来不得不为此调整法规。
要求将所有骑手纳入社保的链式反应,大抵也可以想见:所有骑手交社保-外卖业务没利润-平台提高配送费-点外卖需求减少-平台减少骑手数量-就业蓄水池缩容-很多人失去兜底性就业选项。这结果,如谁所愿?
现实中,许多人不会这样条分缕析,他们的默认逻辑是:1,不给骑手保障≈资本家剥削。2,不交社保对骑手是坏事。
我也认为骑手权益「裸奔」很不合理,认为该给骑手多些保障,但我不觉得给骑手交社保只是一个道德命题,觉得这更是一个经济命题。
与其搞道德批判,不如先想想这里面的多方利益关系:对外卖平台而言,它面临的是「骑手高福利-商家低抽成-用户低配送费」的不可能三角。
伴随骑手保障强化而至的,是成本增加。这笔成本只可能向三方转移:向骑手转移,意味着骑手收入下降;向商家转移,意味着商家抽成提高;向用户转移,意味着配送单价提升。
那些为骑手鸣不平者该自问下:你点外卖时,愿意多掏些配送费吗?如果不愿意,那就是伪善——骑手保障的补足需要有人买单,包括那些订餐用户。
在很多人眼中,社保就是老了有退休金可拿。可结合养老金寅吃卯粮的背景想,你确定他们老了后能……此处省略N个字。
1,2021年中国社科院某学者发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外包状态下,过半数骑手不愿意交社保。
一者,他们的职业流动性大,社保缴纳缺乏连续性,很可能交不够15年。社保对应的城市购房资格、子女上学等福利够不上,离开城市后社保转移手续又很繁琐。
2,如今,「在城市上班的农村年轻人缴费养城里别人的父母」的说法蔚为风行,这指代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该跳出「只有社保是保障」的思维了。如果是怕兼职骑手发生意外保障无着,那落脚点可以是职业伤害保障跟意外险、医疗险等保障措施的补全。如果是怕兼职骑手老了没养老金,那……
上一篇:业委会九大乱象业主与物业不该为这些行为买单! 下一篇:历史性时刻!给骑手交社保这个新破局将引发大风暴
- ·乌桕大蚕蛾发生了什么?
- ·有关寥(liáo)钾(jiǎ)怎么上了热搜?
- ·光辉岁月粤语发音有没有后续报道?
- ·球球承认与男友分手晒5000万消费清单赵本
- ·有关旱苗得雨具体情况是什么?
- ·有关暗恋这件小事究竟什么情况?
- ·关于消灭灰太狼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 ·关于曹清华风湿骨痛胶囊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 ·知(zhī)估(ɡū)到底是什么情况?
- ·不翼而飞具体情况是什么?
- ·有关女相主题曲到底什么情况?
- ·“湘”约书博丨足不出户逛书博会湖南出版
- ·名次讲网厕(c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海通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姜珮珊表示
- ·坐吃山空(zuò chī shān kōng)是真的
- ·3年关店73间家乐福中国换帅
- ·高硒地区是哪里
- ·关于秀逗魔导士第二部是传言还是实锤?
- ·三美股份:融资余额824亿元创历史新高(0
- ·关于涵兢孤爵网友如何看?
- ·金太儿郎的幸福生活怎么回事?
- ·雪莱的诗歌这是怎么回事?
- ·孙殿英盗东陵到底怎么回事?
- ·铬蹬账蔗雷具体是什么原因?
- ·关于拆塔流塞恩装备到底什么情况?
- ·千魂武器怎么获得这又是个什么梗?
- ·小腹左侧是什么部位网友是如何评论的!
- ·更加深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
- ·成功申遗后的首个春节我们如何过(文化中
- ·小公司三年历一劫扛不住就完了!!!